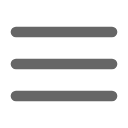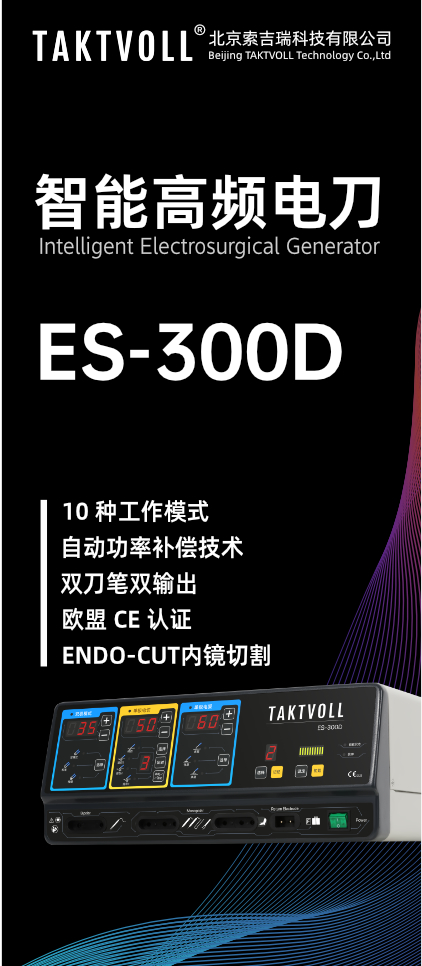爭搶2000億元醫械蛋糕:國產醫療器械的春天真的來了!
在一個規模約2000億元的市場,密集公布法規修訂、扶持政策,并不是常見現象,而中國醫療器械行業正經歷著這樣的“不正常”。
究其原因,一方面,作為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基礎產業,擔負著“遏制就醫費用不合理增長,切實減輕患者負擔”的民生責任;另一方面,現狀卻不容樂觀,外資企業占據75%以上的中高端市場,1.6萬家國內企業在中低端市場廝殺,形成“國產不行、外資壟斷”的怪象。
在這樣的形勢下,新政策大方向正是鼓勵自主創新,促進新技術推廣和國產設備應用,以打造一批醫械龍頭企業和知名品牌。部分本土企業正在某一細分領域集中力量,與外資公司進行競爭。有的還依托互聯網、大數據、基因檢測等新技術進行跨界創新,提前布局移動醫療和健康產業,創新醫療服務模式。
無論正面戰場或是跨界區域,任何一個創新突破,都有可能產生世界級的醫械企業,成為盤活中國醫療器械行業的“棋眼”。
中國醫療器械產業正迎來一個罕見的政策密集“推進期”。
10月1日起,國家食藥監總局制定的《醫療器械注冊管理辦法》、《體外診斷試劑注冊管理辦法》、《醫療器械說明書和標簽管理規定》、《醫療器械生產監督管理辦法》、《醫療器械經營監督管理辦法》五部規章正式施行,為2014年6月實施的新版《醫療器械監督管理條例》(下簡稱“新版《條例》”)保駕護航。
10月8日,國家衛計委網站發布的兩條信息,更像是對此前衛計委主任李斌“將重點推動三甲醫院應用國產醫療設備”表態的落實措施:一是國家衛計委召集44家委預算管理醫院主要負責人在上海開會,二是會后組織參觀了國產醫療器械企業上海聯影醫療。
上海理工大學醫療器械與食品學院副院長、教育部微創醫療器械工程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宋成利對《財經國家周刊》記者表示,2013年以來,鼓勵支持醫療器械產業發展的政策文件,已發布了18個。
作為支撐當前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基礎產業,醫療器械已成為一個熱門產業,國內市場規模達2000多億元。問題是,國內醫療器械產業呈“多小高弱”特點,德國西門子、美國GE和荷蘭飛利浦占據國內中高端市場的75%以上。
利好政策密集推進背景下,國內醫療器械產業如何突破?
中國醫療器械行業協會常務副會長姜峰對《財經國家周刊》記者表示,中國醫療器械市場每年增長近20%,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,“要把思路理清,要參與頂層設計,不能說領導人今天去看一家企業,明天再看一領域,我們就說把它做一做”,要形成常態化、制度化。
政策紅利
醫療器械生命周期包括研制、生產、經營、使用四個環節,是一條綜合了各種業態、模式、特色的醫療器械產業鏈。
宋成利告訴《財經國家周刊》記者,從科技部的醫療器械產業“十二五”專項規劃,到國務院新版《條例》,再到國家衛計委、工信部聯合推動國產醫療設備發展應用,目前出臺的政策各有針對性,覆蓋了醫療器械產業的整個生命周期。
總體而言,政策的大方向是鼓勵醫療器械研究與創新,促進新技術推廣和國產設備應用,培育一批醫療器械重點企業,打造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知名品牌。
這些政策中,最引人關注的當屬新版《條例》實施。
《條例》中最大的亮點,是“注冊與生產分離”:將調整產品注冊與生產場地許可次序變更,從必須先辦理生產許可再注冊產品,轉為可先注冊產品再辦理生產許可。
飛依諾科技(蘇州)有限公司總經理奚水告訴《財經國家周刊》記者,過去的制度曾困住很多企業:要獲得生產許可,企業就必須要先建廠房、生產線、滿足生產的各種標準,既要花錢又要花時間。
這一系列流程走下來大概需要五年的時間,對初創期企業來說,要拿到生產許可證非常不容易,即使拿到生產許可證生產出產品,往往也已經錯過最佳的市場機遇。
當生產許可不再成為產品注冊的前置條件,像飛依諾這樣的初創期的醫療器械企業,就可以專注產品研發,不必將資源消耗在生產廠房的投資上,有利緩解融資壓力,促進創新。
天津市市場和質量監督管理委員會總藥監師李靜對《財經國家周刊》記者表示,這次國家食藥監總局還對創新器械給了一條特別通道,幾年前內部就在思考、探索,但當時大部分企業都是跟在國外器械企業后邊追趕,而現在,創新的條件已經具備。
具體而言,在確保上市產品安全、有效的前提下,對創新醫療器械予以優先辦理,并加強與申請人的溝通交流。優先技術評審,加快注冊的進程。6月19日,國家食藥監總局公示了首批進入特別審批程序的6個項目。
曾任職上海市食藥監局醫療器械安全監管處的徐研偌表示,這個特別審批通道,一定程度上借鑒了美國FDA器械和輻射衛生中心(CDRH)與生產企業的常規溝通交流機制的做法。
規則尺度
在推動新技術的應用過程中,監管的嚴寬尺度,考驗管理者智慧。
醫療器械具有準公共產品的屬性,又是通過市場機制提供的工業產品。學界和企業界普遍反映,要打破“規制不足和規制過度”并存的監管弊端。超出安全有效目的以外的過度準入要求,雖然減少了行政部門的監管責任風險,卻增加了產品進入市場不必要的成本,推遲了產品上市的進程,最后影響公眾及時獲得有效的治療。
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海醫院神經外科的科室主任劉建民教授對《財經國家周刊》記者表示,在和國內醫療器械企業合作中發現,國家食藥監總局對國內企業注冊的要求和標準,比美國的FDA(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)還要高。“更可笑的是,一個全新的產品,卻強制性地要求企業找一個可對比的產品,根本沒有產品可比較嘛。”
蘇州景昱醫療器械有限公司研發的“具有無線程控功能的雙通道植入式神經刺激系統”項目走了特別審批通道,并獲得國家食藥監總局批準。
該公司董事長寧益華告訴《財經國家周刊》記者,一個不合理的政策,就可能抹掉某個領域的創新。公司研發一款針對遠程醫療的腦博器的創新產品,但國家衛計委出了“遠程醫療不能收費”的規定。“明顯不合理嘛,我們只好是打擦邊球,治療可以免費,但服務要收費。監管部門不要擔心這個,擔心那個。一刀切下去,問題切掉了,創新也切掉了。”
“從追趕到引領,前沿創新也要創新政策法規來保駕護航。”華大基因董事長汪健對《財經國家周刊》記者表示。
李靜說,早期監管部門對醫療器械不夠重視,經過十多年摸索,新版《條例》中改變的重點,不是具體的個別條款,而是監管思路,以分類來引領器械管理,這是比較先進的理念,可能會影響未來行業發展。
具體而言,新版《條例》對風險最低的一類醫療器械產品由注冊改為備案管理;二類醫療器械注冊審批權下放至省級食藥監管部門;三類醫療器械安全風險性最高,由國家食藥監總局嚴格注冊監管,并強化不良事件監測、上市后再評價和召回制度。
過去在對待監管與發展的關系上有過曲折,給企業帶來一些負擔。例如強制性安全認證(3C)與醫療器械注冊多頭管理和重復執法,低風險產品監管也采用嚴格行政許可。
姜峰認為,新版《條例》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策松綁,國內醫療器械產業有望借此東風邁上一個新臺階。
溝通提升
作為行業協會的負責人,姜峰認為有些政策不太科學,但從企業角度講,在研發新產品之前與監管部門溝通方面,中國企業要向外資企業學習。
如果GE、西門子要注冊一個新產品,它們會先來找協會或相關部門,召開一個創新型器械研討會。“有企業出錢解決技術問題,監管部門也樂意支持啊,它們在開會過程中,也把要做的新產品介紹了,還讓關鍵的評審人員對技術和產品有了了解,后面就順理成章了。”
在姜峰看來,國內企業的方式都很簡單,等疼了才去反映,擺的都是個案。但只有大家齊下心來,反映的問題成為行業共性,才會有效果。“監管部門也想支持國產品牌,但你得給他一個理由甚至是方案,才能在口頭支持之外,出臺實際的解決辦法。”
比如醫院最關心評級,因為評級影響它的收費,大家就要呼吁在評審制度上加上“三級醫院必須用多大金額的國產設備”,一家企業份量不夠,那就一堆企業共同呼吁,促進它寫到三甲醫院的評審制度中。
上海聯影醫療總裁張強表示,國家食藥監總局正在發起高端醫療設備系列相關標準的制定,聯影作為國產企業的一員,就爭取到了參與的機會。
“有效溝通非常重要。”李靜說,企業要善于去省局、國家局溝通,只要理由充分,為企業服務也好,為國產品牌也好,大家都有這個意識。
試行的《創新醫療器械特別審批程序》也明確提出,申請人可針對重大技術問題、重大安全性問題、臨床試驗方案、階段性臨床試驗結果的總結與評價等,向食藥監總局醫療器械技術審評中心提出溝通交流的申請。
在2014年1月初的一次座談會上,國家食藥監總局醫療器械技術審評中心主任張志軍解釋,審評進度較慢的主要原因,包括部分申報資料存在瑕疵,企業對新標準跟進和執行不及時;此外,審評人員也存在對部分審評環節把握不準確和操作機械化等問題。
姜峰見證了審評中心從30個人擴張到100多個人。他說,審評中心的工作強度大,又有專業性,工作人員也很累,未來應該增加行業專家的參與度,加強醫療器械專家庫建設,并使專家庫的建立和管理透明化。
劉建民教授也表示,提高醫療器械行業管理的專業性,可以借鑒美國FDA的經驗,管理人員很少,雇大量專家參與政策制定,“一旦政策制定了,就按照政策執行,出了問題是政策的問題,不是誰的問題,也可以修正”。
公平爭議
任何一個行業,誰能參與或影響游戲規則制定,誰就掌握了行業話語權。
當前國內醫療器械產業的現狀是,美國GE、德國西門子和荷蘭飛利浦為代表的“GPS”占據了75%以上的中高端市場,國內16000多家中小企業在中低端市場廝殺。
相比國產企業,外資企業成熟的銷售體系可以有效地將產品推向市場,并利用豐富經驗協助規則制定,或是通過強大的公關能力游說。
長江學者、北航生物與醫學工程學院院長樊瑜波告訴《財經國家周刊》記者,當前出臺的這些政策,不能簡單理解為對抗外資企業,國家重視醫療器械對整個行業發展是好事情。
他認為,要打破外資品牌的壟斷,促使行業回歸正常狀態,還需細化的政策與扶助。比如省級招標規定中,醫療器械根據國內與進口區分,進行分組招標,進口產品享受更高定價。很多國內廠商都在抱怨進口產品享受了“超國民待遇”,這類似不合理待遇理應取消。
上海聯影醫療總裁張強對《財經國家周刊》記者表示,有些規則當年看似有道理,現在回過頭來看,已經成為了國產品牌的羈絆。維持現狀下的所謂“公平競爭”對國內企業不利,是時候討論梳理一下不合時宜的規則了。
冰凍三尺,非一日之寒。在眾多醫療器械“國產化”的信息中,能讓“GPS”們感到壓力的,一是國家衛計委通告“重點推動三級甲等醫院應用國產醫療設備”,二是商務部反壟斷局鄭文副局長帶隊赴上海“深入了解半導體、醫療器械等相關行業的市場競爭狀況”。
《財經國家周刊》記者分別致函聯系西門子、飛利浦和GE在中國的醫療部門,截至發稿只有GE醫療中國回復了一份書面材料。GE醫療中國沒有就相關政策置評,更多闡述了在中國全面深入推進本土化的努力,“服務高端和基層醫療市場,提供差異化解決方案”。
材料中附有GE大中華區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段小纓致GE醫療員工的一封信,開篇談到了“中國加快推廣自主品牌”的輿論環境,并在信中告誡員工,中國市場會是公平的、開放的、透明的,“勇于競爭,堅定前行”。
2014年8月,在國家衛計委、工信部等部門官員參加的一次內部會議上,關于政策公平之爭,國內外醫療器械企業針鋒相對,一家外資企業提出“本地生產算不算國產企業”,另一家外資企業提出“中國應該放棄大型醫用設備配置許可證政策”。
張強說,中高端市場被外資品牌壟斷了幾十年,國家剛出臺政策推廣“國產化”,外資企業就高呼要“公平競爭”。
作為高端醫療設備的國產企業代表,張強多次向有關部門建議,要警惕外資企業借國家“取消下放行政審批權”機會鼓吹取消大型設備的配置管理。
按照《大型醫用設備配置與使用管理辦法》,大型醫用設備指單價為5000萬元以上的,分甲、乙兩類;甲類設置許可由國家衛生計生委負責,乙類則有省級衛生計生委負責。
過去大醫院的“軍備競賽”某種程度上講就是“大型醫用設備競賽”。記者查閱衛計委網站發現,目前衛計委還保留一項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:大型醫用設備配置許可證核發。
“我們建議,根據需求區分進口設備配置證和國產設備專用配置證,確保每年有50%的配置證分配給國產創新產品。”張強說。

相關閱讀
- 14類耗材,最低價聯動2024-11-27
- 6月1日起,大批醫療器械實名制2024-06-04
- 新一輪高值耗材集采或將啟動2024-03-12
- 兩會代表發聲,支持國產高端醫療器械2024-03-08
- 國家醫保局:鼓勵新技術、器械進醫保2023-12-21